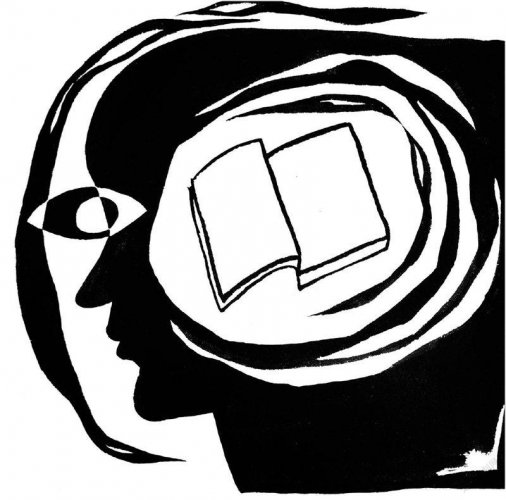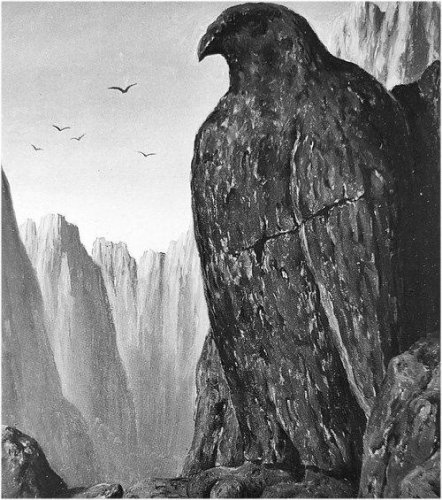海外散文:一个拐弯(19)
旅日漫记
谁能双手捏着这笛子,轻轻地,一扬,一挥,一吹,就将宇宙里的一切都吹到宇宙之外呢?那是灵魂一种随心所欲的吹奏,还是一种没有根据的逸出?
宇宙之外的世界,更是一支比宇宙大了长了无穷倍数的笛子,这是必然的。还有宇宙之外的之外吗?还有必然的必然吗?
我的脚,迫不及待踏在自己沉重的脚印上。赶快逃离这个神经兮兮的青山通,可那黑狗还叨着一个血腥的舌头呢。
“只要我活着,猫就不能不杀,就不能不收集猫的灵魂……已经腻了,累了……又不能自己提出不干。
而我连杀死自己都不可能……只能委托別人。所以我希望你结果了我……”
乞求他人杀死自己,这也是一种笛子,或者笛子的一种灵魂吗?
“可是中田君……这东西你必须理解。战争就是一例。战争你知道吧?”
我不是村上春树的中田君,你没有资格责问我。
琼尼·沃克用食指尖对着中田的前胸。“呯!”他说,“这就是人类历史的主题。”
为什么不换一个主题呢?或者恢复笛子本来的旋律。
“你必须这么考虑:这是战争,而你就是兵。现在你必须在此做出决断——是我来杀猫,还是你来杀我,二者必居其一。”
村上春树来了。他在小说中叙述:中田无声地从沙发上立起……毫不犹豫地操起台面上放的刀……
毅然决然地将刀刃捅进琼尼·沃克的胸膛……
“回家吧!”中田对猫们说。可他站不起来了。
我是东京的匆匆来客,也站不起来了。正月的寒风从夜晚的脚底下灌了进来,直往胸腔里渗透。我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一块小石头长了起来,硬邦邦地哽在喉咙里,可吐不出来。
DENMARK HOUSE 的牌子好像一排子弹,哒哒哒一个连发,将灯的影子打倒了,一摊一摊的血,黑黑糊糊,向着没有方向的方向流去,拖着没了声息的尾声。
那猫血淋淋的灵魂被解救出来了吗?我可一只也没看到,也不愿意看到,包括琼尼·沃克丑恶的、扭曲的灵魂,包括被生物界、人世间、宇宙里的所有战争所杀戮的所有灵魂。但村上春树仅仅把它的一些事件记录在案卷里,便写成了畅销小说。村上春树该是能通灵的人吧。
我受不了血腥味的呛,赶紧登上公交大巴到了丸之内1 丁目。东京车站外的火车头不冒烟了。大白天我大摇大摆地走过的时候,都是绿色的、褐色的、灰色的枝条和叶子,有形有状,一圈又一卷。可现在却是一片又刺眼又空洞的幻影。你是谁的手,把我的睫毛拔掉了?
人呢?逛街的人,赶路的人,进出车站的人,一个都没有,只有一些人的影子。大概猫魂回来了,活生生的人就跑光了。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所谓的人。比如日语里的“人”,英语里的“people”,都是所谓的人凭空制造出来,又包装为文学上的人,就不是本来的人了。
相关阅读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