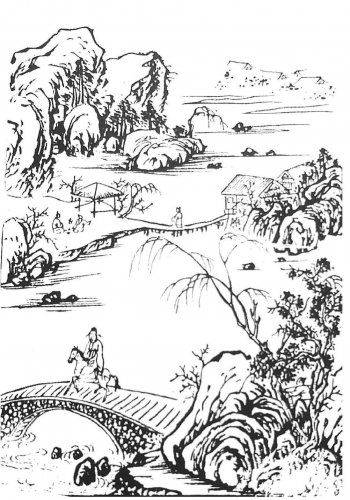生活随笔:草原的歌曲(2)
想起了哈扎布
遗憾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蒙古长调这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人们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今天,渐渐萎缩成了一种点缀。
大约十多年前,我怀揣梦想去锡林郭勒旅行。那时,草原深处的旅游景点还算得上是古风犹存,我想在草原上以面对面的方式听到牧民歌手的歌唱。走进一座硕大无比的迎宾帐篷,在闷倒驴和手把肉的香气儿里,一位皮肤黝黑、身着蓝色绸缎蒙古袍的中年汉子用荡气回肠的长调,把我唱得泪流满面。泪水顺着下巴不停地滴答,音符一样斑斑点点,打湿了我白色的短袖T恤。终于忍不住了,我点了哈扎布的《小黄马》。可是,那个已经用歌声把我们镇服的中年歌手却面露难色,用生涩的汉语说:“我不会唱《小黄马》。”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帅哥歌手凑过去,有点儿不服气地问:“谁是哈扎布?”中年歌手面色肃穆地说:“歌王哈扎布。”小帅哥一脸迷茫。显然,他不知道哈扎布,更不知道《小黄马》。后来,中年歌手又特意走到我身边,深深鞠了一躬,满怀歉意地说:“我为您唱一首别的吧!”我赶紧站起来还礼。因为,这一躬不是鞠给我的。那天傍晚,坐在舒缓的草坡顶上向四边望,除了我们那几顶帐篷,方圆十数里“尽荠麦青青”。远处的帐篷星星点点,看上去比蘑菇还小。太阳落进草棵里的时候,天和地一片金灿灿的黄。我仿佛被镀了金,心里静静地回旋着哈扎布的《小黄马》,却照旧一句也唱不出来。夜晚,下起了大雨。八月盛夏,我一次次起身,往矮胖的蒙古炉子里添加晒干的牛粪。雨鞭噼噼啪啪打在帐篷顶上,叫人觉得像是住在一面被使劲儿敲击的大鼓里头。宏大的雨声回音阵阵,像是阵容强大的伴奏,心里面回旋着的,依然是哈扎布比天籁还要悠远的歌声。“小黄马啊,小黄马,你那轻巧的步伐令我陶醉。年轻美丽的姑娘啊,你那温柔的性格令我心碎。”长调字少,曲调长,拢共两句话,唱出了说不出的情感和韵味。后来我查了一下,夜宿的地方,离哈扎布的阿巴嘎诺尔旗只有百八十公里,“歌王”退休以后就定居在自己最初降生的地方,与马匹、青草、牧民和光同尘。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有定数,只不过我们因为灵性的级别太低不知道而已。
晚年,哈扎布曾对席慕蓉说过这样一段话:“面对死亡我并不惧怕,此刻我的心就像那佩戴着银鞍子的骏马,又像那心里有着私密恋人的喇嘛一样,兴高采烈地往前走啊走啊!……”这种乐天知命的态度,既源于他对生命自身规律的尊重,又体现出对自己八十多年人生的总结与自信。他的骄傲与自豪,当然还有尊严,是谁都无法剥夺的。就在我知道哈扎布并尽其可能反复听他所有的歌曲之后大约两年,2005年10月27日,八十三岁的哈扎布去世了。至今,我依然为有幸在这个世界跟腱在的哈扎布以歌声为媒介神交而欣慰自豪;同时也很遗憾,没有能够像在露天大剧场里晃动荧光棒的“迷弟迷妹”们那样,及时产生一个去阿巴嘎纳尔旗拜访“歌王”的想法,以至于如今只能在电脑前委委屈屈地戴着耳机,一遍又一遍听《小黄马》,听《苍老的大雁》,听《轻快的走马》……哈扎布去世29天后,蒙古族长调民歌成功人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我知道,尚未走远的哈扎布老先生一定能听到这个他生前念兹在兹的好消息。
相关阅读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