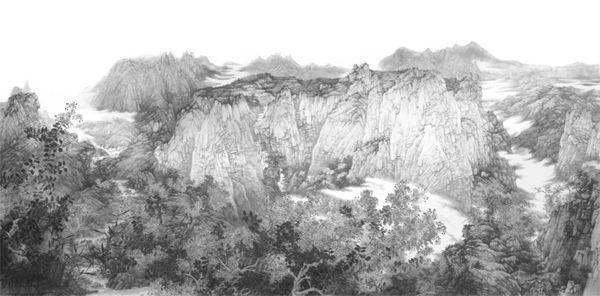生活随笔:初春的柔光
伸向墙外的香椿

初春的柔光一束束地滑落在老家后院里,母亲头一撇,对我轻轻地说:“长椿叶芽儿啦!”
在这院里,最能成为风景的大概就是这些椿树吧。苏醒了的精灵们,是我和母亲从老宅古井边的窗台外,一蔸蔸地移植过来的。
此刻,相逢正是怀念吧?
三年前的那个周末,我陪母亲在老宅菜园里侍弄青菜地,短憩时,我指着两棵枯死得差不多的老树说:“这树还有用吗?不如烧掉它们哩。”
沉默了好久,母亲喃喃念着:“多可惜的老椿树。要是新屋那边也有几棵就好啰……”
我知道,老人家有对行将逝去生命的惺惺相惜,也有对生命承继的期许。看到她落在老椿树上的目光,我的思绪越过这菜园墙头、越过这瓦蓝色的天空,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
那时的老宅其实是爷爷、我家、伯父家,还有血缘较近的两宗亲的居住综合体,以一问大厅堂为轴心,滴水檐前后勾连,用的都是土砖烧瓦。黑漆漆的,像几只土狗崽似的趴在田垄边。
我们这一栋连体老宅,虽然户数少些,但比起聚居在附近的其他家族宅子显得更有生气些,或许因着那片小林子。小林子盘踞在一口池塘上方,挺拔的梧桐和樟树,溜圆的杉柏,浓密的油茶,低矮的野蔷薇,还有芬芳的桃李,当然,最难忘的还是那倚在墙根边儿两棵硕大香椿树了。有了这些轮回四季的高低搭配,整个林子显得阔绰而热闹,大人们的希望、小孩儿的欢乐,甚至连小禽兽的撒泼都藏在里头。
总是巴不得冬天早早地结束。初春里,农人的蔬菜品种并不多,最给人希望的最莫过于林子中的椿树了。两棵粗壮的野椿树,伸出众多的枝丫,一立春便将蓄积了整个冬天的营养绽放出来。光秃秃的丫杈上星星点灯地破顶儿了,风雨一来,赶趟儿似的收拢了紧绷的芽顶儿,露出了“小红帽”,只一袋烟的工夫就多了几棵嫩芽,红红酱酱的,像刚点着的火苗“扑哧”地腾跃。再过一两天,攒紧的芽尖顶膨胀着向外舒展,变成鲜嫩的椿叶,阳光下,红中带绿,翠中闪银。要是再忍着点儿,芽苗成叶,枝上拔节,枝上长权,权上又长嫩芽……
蓬勃的长势,喜煞了众多的母亲和孩子。椿叶芽之于农人,就是大地赐来的菜肴,竟然得来全不费工夫,而且韭菜似的可以收获几茬。
开摘了!母亲取出带镰钩的长竹竿,牵引着我们的目光,轻轻地伸向那些鲜翠欲滴的嫩芽细苗。芽苗密密麻麻的,昭示着林子的膏腴和慷慨。
只听见“咔嚓”几声响,芽苗一簇簇、一团团地纷纷坠下,向松软的地面下了一场椿叶雨。
我们赶紧收回惊诧的目光,拎着竹篾篓子、篮子跑过去捡拾,只觉鼻子底下阵阵椿香袭来。母亲回家,先把椿树芽苗用滚烫的沸水快焯一下,捞出来后沥干水,用手掰开嫩苗权,然后切碎了拌入鸡蛋浆中,打圈儿搅匀,油炸后端上四方桌,椿叶蛋香即刻弥散了一屋子。尝蛋花的场景至今仍是记忆深处最幸福的时刻。
相关阅读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